本文从新闻报道与散文随笔两种不同写作体裁的交融、契合,探讨以名胜
古迹为报道对象的游记类作品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但愿本文能对网友
撰写旅游博文及人文摄影创作也有所裨益。
新闻与文化的契合
——对名胜古迹报道的思考
马恒健
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我,自2005年起,以5年的时间,自驾纵横蜀地10万里,以泛新闻的写作意识和大特写式的写作手法,写出70多篇对川内名胜古迹的报道,并全部在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2009年底,我将其中的55篇集纳成册,出版了《蜀地秘境》一书,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四川。书成之后,我对自己数十篇名胜古迹报道的采写体会进行回顾,力图得出新闻大特写与文学类游记的交融、契合的一些体会。
涉及巴蜀大地的山川景物描绘,历史上不乏佳篇名作,但相关专著并不多。明代文献学家、曾任四川右参政的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以其平易流畅、博采众长的体例而独树一帜。此书中,曹学佺提出一条山水文学的创作原则:“以吾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两事,好之者不作两人。”人与山水的融合无间,同样体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现代徐霞客”之称的朱偰先生《漂泊西南天地间》一书中。
要做到人与山水的融合,“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两者缺一不可。“旷世游圣”徐霞客将其理念引申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万言书”,写下了叹为观止的260万言的《徐霞客游记》。因为有了这部卷帙浩繁的游记,才有了古代人文地理知识的传承,并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正是这些古代旅行家踏遍青山的精神的感召,使我作为一个新闻人,更希望自己以实地的踏勘和详实的采访,将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和游记写作的一般准则结合起来,以新闻的可信度和游记的感染力传播积淀深厚的巴蜀名胜。一篇篇名胜古迹报道刊出后的反响证明,这样的写作手法,做到了读者群的相对多样化、受众的相对扩大化、历史文化传播的相对广泛化,使许多“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化胜迹广为人知。梳理这些体会,我认为做到写好名胜古迹报道,需要贯彻三个“两结合”的原则。
一、新闻性与史料性
五年里我所涉足之处,一部分地方仅仅是准备开发,一部分地方甚至尚未纳入开发计划。因此,我的游记中的部分内容,就鲜为人知或仅有所闻。但是,这些地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奇绝秀险的自然风光,既令人叹为观止,又使人丰富知识。比如,十几座南宋抗蒙时期分布在四川几条大江及多处关隘的“宋城”,不仅令人惊讶地遗存着城门、城墙、碑刻、造像,其山形植被也令人赏心悦目,是历来旅游文字很少涉及的领域。因此,这些人文历史遗迹的发现和披露,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价值。尤其在人们苦苦寻觅新鲜、罕见的旅游目的地的当今,这些内容更加吸引读者的目光。
又如,令仗剑远行的李白暂停匆匆步履、从而吟哦“峨眉山月半轮秋”的平羌江小三峡,被称为“军防要塞式住宅奇观”的武胜宝箴塞,大熊猫作为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地夹金山邓池沟天主教堂等等,这些当今游人较少地涉足之地,不少读者在阅读了刊登于报刊的报道文章之后,纷纷自驾前往。
类似的这些人文遗迹,在历史学家或文学家眼里是宝贝,但要为多数游人欣赏并愿意前往,就必须发掘其承载的人文史实,从而使游人的感受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新鲜,而是产生心灵的一定程度的震撼。在搜集和获取这些沉淀于浩繁的典籍和湮没于民间乡野的史实时,我的新闻采访经验及手段也发挥了作用,呈现出来的就不仅具有新闻报道应有的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厚重感。
比如,金堂云顶城巍然屹立于沱江畔,山上有金碧辉煌的慈云寺,且林木苍翠,是成都市民游山玩水的好去处。我在《云顶擎天一石城》一文中,不但谈到了云顶城修筑的缘由,且从遗存的城门拱顶上考证出南宋时期筑城的确切时间及守城将领的姓名,从而使游人对这座在乱世之中曾为成都府治所的云顶城,有了崇敬和肃穆之感,使游人不但游玩于美景中,也穿越于历史中。
又如,昭化古镇经过打造,游人日渐增多,但那句“到了昭化,不想爹妈”的俗语到底出自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在《昭化 蜀汉王国的第二都城》一文中,用翔实的史料证明了“到益昌(昭化),忘爹娘”一语出于武则天母亲之口,从而使历史文化名镇昭化又平添几分吸引力。
二、新闻性与文学性
在写作手法上,我将新闻性与文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本着眼见为实、真实记录的原则,我书中涉及的地方,均一步一个脚印的详加踏勘、细心观察,以准确、平实的文字对所见的实物实景进行记录,力求直观、形像,尽可能给读者以较强现场感。
比如,我如此叙述南宋抗蒙古城凌霄城的上山秘道:“宽仅1尺多的山道上铺的不是石板,而是比马蹄大一点的不规则石块。它块块厚实,表面平整,如牙齿般牢固地镶嵌在泥土之中。”如此这般,读者对这条秘道就有了临场般的印象。
再如我描写邓池沟天主教堂内景:“近300平方米的厅堂里,只见10根1尺多粗的圆柱,支撑着交叉穹窿的拱顶,使屋顶显得高远、幽深;两侧是间距很小的一溜窗户,窗框的上部呈尖弧形,窗门用细木条交叉成密密的棱形眼孔。”
此书中的文学性,主要是表现“游感”上。从文学性的文字在整篇游记中占的篇幅来讲,要把握一个份量多少的问题;从抒情感怀的语句在整篇游记中所表达的情绪强弱来讲,要把握一个程度深浅的问题。游到精彩处,情之所至,诗情画意般的言辞自然而然而来,绝不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
比如,在我的《高颐阙 夕阳下的汉魂》一文中,是这样抒发当时的心情:“厚重的大门推开了,一股苔藓的气息扑鼻而来,很容易让人想到秦砖汉瓦,想到唐诗宋词。大门内外,相隔千年;红墙两侧,古今泾渭。”
再如,平羌江小三峡的人文底蕴和青山如黛、绿水中流的美景,令我在《平羌小三峡 月出峨眉照江流》一文中,有了如此感怀:“李白走了,那平羌江中碎银般的月影,便成了乡愁,成了寄托。其后的许多墨客骚人,或因为激发文思、寻觅灵感,或因为瞻仰美景、垂涎美食,踏着李白的足迹来了。”
正是由于我书中的多数文章既具备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又表现了空间和时间上的想像力,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从而使这部游记更为耐读,使读者不仅仅因猎奇而读。
三、新闻性与思想性
新闻性属理性的范畴,思想性属感性的范畴。这两者在游记里反差较大,是不太容易处理得和谐、自然的两个方面。
我这部游记的55篇文章,基本按所到之处的游历路线、观赏顺序来叙述,并在文章里毫不牵强地融入路程、路况、路线及食宿、气候、海拔等信息,这些都大致体现了新闻的基本要素。我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使读者提高游览的效率,尽量避免因走重复路线而产生的单调感,在单位时间内尽可能的多看、多玩;二是避免读者在游览后产生遗珠之憾,路程和景点依次罗列,哪个地方停留多久,哪个地方要着重游览,读者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时间松紧以及兴趣爱好作合理安排。
如果通篇如此,显然只能算参观指南、旅游手册。将思想性、哲理性融入其中,则可以给读者深层次的启迪。这种启迪,可能使游人在了解事实、明白真像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以此校正自己的人生坐标。
比如,当我站在南宋的半壁江山最后一个被蒙古铁骑攻克的城堡凌霄城上时,面对凄凉而又悲壮、荒芜而又充满生机的场景,如此写道:“我们能够往以前看多远,我们才能够往未来看多远。古人留给今人的那一笔宝贵财富,将会让我们走得更远。”
再如,我在邛崃火井镇游览了世界第一口天然气井----汉代古火井后,写了《火井 汉代的火焰仍在升腾》,此文如此结尾:“六角井的火焰早已熄灭,但它留下的火种早已燎原。这火种跳跃在我们每家每户的灶台上,把历史和现实浓缩在咫尺之间。”
又如,我写的《天雄关 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剑门关的门槛”天雄关来形容和歌颂卓越人物:“它曾经沧海,而今与春华秋实为邻,与清风明月相伴,如同功成身退的智者,蛰伏于祟山莽林之间。英雄不死,他只是渐渐隐去。”
我写这部游记的初衷是为旅游者提供更多出行目的地,以及满足一些不仅仅是休闲的旅游者劳其筋骨、磨砺意志的需求。出乎我意料的是,书中的这些具有一定思想性、哲理性的语句,同样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以网上发帖、以撰写的散文随笔的方式,整段引用,并在琢磨和诠释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悟。
要写出一部给读者带来惊喜,使游人产生新的兴奋点,且能经受得住时间检验的游记,还应该在纯写作之外做足功夫。
首先,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这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终身追求。在狭隘的风景主义美学观大面积占领旅游空间的时代,人们在纵目山河、寄情山水时,更需要具有敏锐触觉的新闻工作者去发掘那些潜藏在风物之中的人文底蕴,使我国大好河山的岚烟与流云,成为大地举托的黄金。而任何一个景致缺乏人文历史的支撑,充其量不过是纸风景而已。
为此,游记作者人文历史知识的多寡,以及对描写对象人文底蕴的发掘程度,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游记的优秀与平庸。除此之外,尽可能地具备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地理知识。这样,既可将每一个景区写得各具特色,也可应对自己在旅游考察过程中自然条件带来的麻烦甚至危险。这些知识以及技能,一方面靠平时的学习、积累,一方面是在出行前做足功课,对目的地的一切情况详尽了解。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把游记写深写透。同时也可避免生活常识和历史文化的表述谬误。
其次,要锻炼自己的一双“发现者之眼”。从宏观上讲,要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之中,发现当下及将来人们可能注目且值得注目的地方,并通过自己的游记使他们的目光聚焦于此。发现固然有别于发明,它不会像获得的专利那样令人瞩目,也不像纯粹的新闻那样具有轰动效应或爆炸性,但发现的魅力,就如同司空见惯的水形成的彩虹,同样吸引着人们好奇的视线。
“发现者之眼”,还表现在实地、现场的观察、探究和与知情者的交流方面。
正如不喜于观察写不出好新闻一样,察人所不察,写出来的游记才有鲜活感。
最后,游记作者应保持新闻工作者的顽童般的好奇心。好奇,是发明的原动力,同样也发现的原动力。厌倦熟视的事物,渴望意外惊喜,虽是人的固有本性,但游记作者的好奇心如果更强烈一些,便能先行一步,为广大旅游爱好者备好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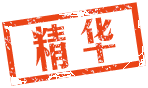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当前版块2016年12月1日之前所发主题贴不支持回复!详情请点击此处>>
当前版块2016年12月1日之前所发主题贴不支持回复!详情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