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清飞这个名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时候,我在铜梁剧团,每次开演前演员扮妆的那一两个小时,场子里的高音喇叭都会播放她的《三娘教子》、《刺目劝学》、《荣归》等唱段。她那莺啼燕啭的唱腔,清亮细腻,甜润婉转,多么地令人陶醉,令人神往。我每次在扮好妆闭目养神时,都会一边耳朵听着她的名曲,一边嘴里轻声地跟着哼哼,努力地模仿她的唱腔,努力地把她的发声发音套进自己戏里的唱段。我常常心里这样想:这位老师长什么样啊?我要是能亲眼见到这位老师那该有多幸福啊。时而又想:我要是也能唱到她那么甜美那该多好啊......那时候对这位师长的痴迷和崇拜的狂热心情,简直就跟现如今的追星族们想迫切见到刘德华等明星大腕一个样。那狂热,一直到我离开剧团那个环境,才渐渐地冷却下来......
不想,几十年后,这些被封存的篇页因为一次偶然,一下子从脑海深处被掀翻出来。那种迫切想要拜见她的感觉就跟潮水一样,一浪比一浪来得更加凶猛和激烈!
想要见她的心情是强烈的,也是不安的。见面前我自己在心里酝酿了许许多多的礼仪用语,但当我真真切切见到她时,却一句都想不起来了,除了怯怯还是怯怯,深害怕自己说错话老师不待见我了。可她给我的印象却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神一般地冷傲不可攀,而是非常的亲和,使我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融入进了她的生活当中。
第一次见面,在短暂的交谈之后,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我与她之间不仅仅是师徒之份,更多的是母女之缘,真是相见恨晚!之后慢慢地接触中,也更加印证了我的这一感觉,我无拘无束地与老师融为了没有血缘的母女。时不时的几天没见到她我就会很挂念她,而且娘儿俩还特有心灵感应,好几次想她了,刚想打个电话,还没等我的问候电话打过去她的电话就到了,我还以为有啥事,一问,她说:“没事,就是想你了打个电话问问”。我答:“我也正说给您打电话哩”。这一问一答,话不多但笑声不断,就跟母亲与女儿间的说话没两样。我啥时想要去看她了,也不用提前给她电话相约,自己径直去。到家了,自己坐,也不用与老师客套,果盘里的零食自个吃,打开冰箱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都自己随意,全然一个女儿回到娘家的感觉。
老师对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很高,细细观察她的生活,感觉她并不像她们那个年代的人。她的思想很前卫,她能够接受许多新的观点和理论,所以她的心一直都很年轻。她把家收拾得既华丽又整洁。虽然经济条件很好,但她从来没请保姆,全靠她和老伴周叔共同打理,一尘不染非常温馨。每年老俩口都会给自己计划出一定的时间出去旅游,把自己的心情和精力调节得相当地轻松和充实,到大自然中去找寻艺术的灵感,使自己的生活和艺术达到更高的境界。
崇高的艺术表演,是她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一生的痴迷,所以我们在一起很多时候自然而然聊天的话题就进入了戏剧。她对我学艺术的要求是很严的,标准也是很高的,一点也不能马虎和勉强。一句唱腔,一个动作——哪怕是一个转身背影,我要是不到位,她都会不厌其烦的给我示范几遍甚至几十遍!她的身段很美,随便一扭就是一个很优雅的雕塑,常常令我羡慕不已。她组织的腔段更是悦耳,能够把你带入那个时空和戏里那种境地,也常常把我听得陶醉其中。遗憾的是,我学不到家。虽然老师毫无保留地教,我也非常用心地学,可我唱出来的“沙昆林”与老师唱出来的“沙昆林”那味就是不一样,为此,我十二万分懊恼。终于,找出一个理由来宽慰自己:何为艺术家?这就是艺术家!我要是也能一下子就学到家了,那不也得叫“家”?这些一点一滴的“味”都是老师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里所积累得来的精华,非我一天两天能学得到家的。
母亲,是一个非常崇高而神圣的名词。在我的心里,左清飞就是我的母亲!或许,是我修了几世,才修来今生与她的母女情缘。我为今生能得到这一情缘而荣幸,我为能有左清飞这位慈祥的母亲而骄傲!我为能成为她的得意门徒而自豪! 本帖最后由 长歌悠悠 于 2013-5-24 15:00 编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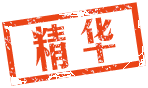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