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灌忆略/肖宗材
按:肖宗材同志,是当年第一批上东灌的水利战士。先是在指挥部宣传队作为骨干成员,后因加强主体工程进口段的宣传工作,奉调去工程六营政宣组与本人一起负责政工宣传。因指挥部隧洞组工作需要便转调那里,仍负责宣传工作。他转战隧洞工程南北上下,历时两年多时间。对龙泉山水利工程,卓有贡献,堪称为数不多的功臣宿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朴实而深情地回顾了“举世盛名”的简阳东灌“天下第一人工地底长河”的创建过程,很是值得大家阅读学习。这对于不忘造福子孙之初心,传承东灌精神,再续家国大梦都是大有必要的,很有价值的!
二0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序言
适逢金秋的前些天,老朋友冷兄林熙真诚而热切地向我提议,可以将原来在“东灌”工作两年期间的经历回忆一下记录下来,宣传出去,既是记录原来那个造福于民的伟大工程的一些情况,也是记录自己的往事,应该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人听了,感慨万千。“打通龙泉山,引水灌良田。”这是当年简阳人民非常迫切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希望能够建成一条隧洞,把流经五指山那边山下双流县太平公社的东风渠的岷江水引到简阳这边来,解决本地经常发生的干旱缺水的严重问题。为此,各级领导做好了各种准备,各区人民热烈响应领导的号召,积极参加工程建设。
那是一个在简阳是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机械化水平极低、土法上马、基本靠人山人海的人力手工完成的浩大的工程。工程高峰时期,参加的干部和社员达10万之众。并且,工程采用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促进了工程按照设计和规划的要求顺利进行。
那时候,本人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能够参与其中,如果要写,写什么好呢?当然,作为一个浩大工程的参与者,自己是亲历了的,确有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也就把原来的实际情况的一点一滴回忆一下而记录下来吧。至于是否写得好,因为水平有限,就请诸位谅解了。
二、在工程指挥部宣传队
本人的老家在现在的高明乡桅杆村二组,即原来的高明公社和平大队二小队。
大约是1970年的春节前后,老家大队的领导找到我说,公社的领导们指示,要我们大队推荐一个会搞宣传的年轻人去东灌搞宣传工作;大队领导们研究决定,就推荐我。他说,他们知道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前两年在本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里表现好,大队的宣传队在参加公社组织的各种宣传活动中都在全公社多受表扬,获得好评。
其实,我在大队那两年的宣传工作期间,就是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期、党的“九大”会议前后,到处都有非常广泛的宣传活动,略有不同的只是宣传的形式和水平而已。
听到大队领导的推荐,本人自然非常高兴,满口答应,表示愿意服从领导的安排,去那里工作,为引水工程出力。
1970年3月,本人刚满19岁,即应召去了五指山半山腰,当时的贾家区五指公社南山庙的龙泉山引水工程指挥部驻地报到,参加工程文艺宣传队。
当时,工程指挥部的政委是杨昌尧同志,指挥长是陈启霖同志。
我们就是指挥部领导下的宣传队。
宣传队的第一批人员大约聚集了二十人左右,都是男女青年人,一般是20岁上下,比我大的有,比我更加年轻的也有。后来又逐步增加了一些人。全体队员中,有的是其家乡当地的青年,有的是下乡知青,有的是回乡知青。
当时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简陋、艰苦的。我们宣传队的驻地都是用竹木新搭建的工棚,都是几人住一个大铺,勉强能够遮阳避雨;大一点的风吹时工棚都会嘎吱作响,令人担心。
我们先在指挥部附近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搬到了山那边的牛心山文家院子住。在文家院子,我们住在比较宽的阶檐搭建的工棚,也是几人住一个大铺。
宣传队的队长即是冷林熙。
我们宣传队的工作任务是:按照指挥部领导的安排,自采、自组、自编、自演一些节目。具体来说包括当时时政方面的;工程方面的则有工程规模、重要意义、灌区范围、受益规模、好人好事、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等等,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有时候是在有关会场表演,有时候是到连队慰问表演。形式则有有线广播、相声、歌曲、舞蹈、朗诵、乐器演奏、传单、标语、专栏、板报、漫画、小册子等等。
本人在宣传队里,参加了一些文艺表演,二胡和笛子伴奏,参与了其他力所能及的宣传项目,协助冷兄和有关同事草拟和整理了一些宣传材料,还管理后勤事务。
三、在工程第六营
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各个隧洞营工作的需要,指挥部分配宣传队人员分别到各营负责政工和宣传工作。
本人和冷兄被分配到第六营即贾家区所建的一个营。驻地在双流县太平公社石板河的小堰口。
营部设置有政宣组、施工组等等必须的管理机构。下设的连队,开始有九个,其中,隧洞连五个、石工连一个、抬工连二个、基建连一个。后来,连队还有增加,最多时是15个。
该营的教导员是彭良浩同志,营长是张世森同志。
当时,营领导先后安排了冷兄、本人、廖君、付逢云、邓菊云、蔡献昌到政宣组,负责有关的政工和宣传工作。
该组组长也是冷林熙。
这个组的工作任务,没有了文艺宣传,其余的与在指挥部宣传队的宣传工作有一些相同以外,还比指挥部的宣传工作多了一些政工事务,其性质要重于原来的宣传事务。
四、在隧洞指挥组
在第六营工作不久,由于隧洞指挥组的宣传工作需要,本人被调动到了隧洞指挥组,与另外一位同事一起,负责除了文艺宣传以外的宣传事务。
隧洞工程,即“东灌”的咽喉工程、关键工程。隧洞长6273.73米,高4.6米,宽3.4米,过水流量每秒33.5立方米。其进口处在五指山那边的双流县太平公社石板河的小堰口,出口处在简阳县这边的五指公社的南山庙下面,即现在的张家岩水库进水处。其高程是,进口处498米,出口处490米,落差是8米。
为了加快隧洞工程的进度,掘进方法除了进水口和出水口两头相对掘进外,工程设计方还设计了14口斜井,即在主洞的上方分头斜向朝下开挖,抵达隧洞水平位置后又再分别向两头掘进。这样,14口斜井就有了28个工作面。
隧洞指挥组驻地在双流县太平公社的山王庙。
组长是姚甫华同志。
指挥组下辖七个营,分别负责各自分工的一段掘进工程任务。
本人在指挥组期间的工作任务:
一是了解工程情况。负责下到隧洞、采石场和其他有关现场,了解工程进度情况,采访当班领导和现场民工,形成第一手资料。有的资料内容向指挥组领导汇报以便提供参考,有的资料内容则写成宣传稿,用当时仅有的油印打印机打印出来下发或者上报。
这种打印机,我还是初学初用。没有师傅专门指点,只是看到了同事使用的方法,自己练习的。
二是及时表扬通报。有的连队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领导要求予以通报表扬(那时候是没有什么物质奖励的)。因此,本人就及时用大红纸毛笔字写出张贴于公众场合的宣传处,或者送到该连队。有时候领导要求很急时,本人甚至不打草稿,经过思考直接书写。
三是举办宣传专栏。令人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的事情是,本人在指挥组举办的宣传专栏,木制结构,横长大约8米,高约3米。每期都计划好最上面的大型宋体或者黑体毛笔通栏标题。下面的面积则计划多少篇内容、多大的小标题、多少字数、小标题和内容是横向安排还是竖向安排、是否安排插画等等。当然,也都是用排笔和毛笔书写。至于插画,则是一些简单的黑白内容。
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都觉得那时候的自己还真是不怕丢丑。因为,自己在当时的同龄人中只能算是能够写毛笔字的青年人之一,尽管当时的农村能够写毛笔字的青年人比较少;尤其是通栏标题中那些一尺左右见方的大字体,本人之前并没有写过,都跟学厨人现炒现卖一样是现学现练的,每次都是预先计划好每个字的尺寸,然后打框,划出字距,书写出来后只能算是见得人,自然算不上写得怎样好。幸好,隧洞组的领导还算大度,没有怎么苛刻的要求于我。
在隧洞组工作期间,另外有一件事难以忘怀。
下隧洞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一身水和泥,而且还非常危险,因为隧洞里确实是曾经发生过伤亡事故的。有一次,本人在隧洞里面采访时,就差点负伤。
那时候的隧洞掘进,先用计划好当量的炸药爆破,然后再用人工挖掘、扩大或者修整上下左右,使其达到设计空间的宽度和高度。
那天我所在的施工面,正好在指挥组驻地附近的埋藏浅、顶盖薄、岩层破碎地段的文家河河床下。那是一个顶上在冒水、上面还有很多松动未落的、带棱角的、大小不等的岩石。当我正在了解情况时,一位连队负责人突然把我一推,我冷不防地往旁边一退,刚好有一个饭碗大小的岩石落在我刚才站立的地方。他说:“你看,好危险啊!”虽然当时下到井下的所有人都戴有安全帽,但是我如果没有被及时推开,说不定帽子已经被砸了,或者帽子被砸偏了以后直接就砸到头上了,或者砸到肩膀了,都有可能的。
那位负责人怎么知道会有岩石落下来呢?因为,他们天天跟那些岩石打交道,已经积累了有关的经验了,他们可以判断岩石的松动情况,可以听出某些响声是否正常。
遗憾的是,当时本人说了谢谢的话以后,就各忙各的了。不久后本人就离开了指挥组、离开了工程回老家了,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位好心人了。
1972年4月26日,隧洞全线贯通;10月1日国庆节,举行了隆重的试通水庆祝大会。本人当时也有幸参观了大会盛况。之后,本人还曾经画了一幅黑白的隧洞出水口的图画,送给了妻弟。
1972年11月的某天,本人还就隧洞通水发过感慨,在日记里写了一首打油诗,即人们平时说的顺口溜:“山隔千年坝丘间,人欲一朝引龙泉。今日银流胜江漫,艰苦奋斗赛过天。”那时候,本人不懂格律诗,只是知道诗词需要顺口、押韵,还自以为就是《七绝》了呢。打油诗的标题是“龙泉流”,“龙泉”二字即指岷江水本身。此作当然只能算是表示一番高兴、庆贺的心情而已。
本人的日记显示,1973年2月25日,隧洞工程正式全部完工交付使用。
五、当时的交通条件
本人为什么想说说这个话题呢?
这与本人当时经历的一件事情有关。
当时,工程上没有什么好条件的公路,仅有一条从贾家镇到龙泉山工程的碎石路。由于工程用的各种大型货车和供应民工生活物资需要的货车多,碎石路多半都被碾得坑洼不平,因此,车子行进中的颠簸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本人的老家到工程指挥部大约10余里。而从五指山这边翻山到山那边的双流县太平公社,父辈传下来的说法是“上山15里,下山15里。”即老家到那边的太平公社大约40余里。这些路都是乡间小路、山上上坡下沟转弯抹角的羊肠小路。当年,那里是没有汽车坐的,我们平时往返于老家与工地之间,都是靠的两条腿。回家时,偶尔遇到同路有到贾家去的车子,就可以搭个便车先到贾家,然后又走8里路回家。因为本人的老家、工地、贾家三地属于近似三角形的地理位置,所以可以临时搭个便车先到贾家再回老家,以便减少走路的里程。
有一次,本人就是这样的搭了领导们的北京吉普。因为是第一次坐那样“高级的轿车”,心里自然非常高兴。
当时,该车已经显得陈旧,在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颠簸前行。 由于本人平时极少有机会坐车,没有适应车况,更没有适应那样的路况,而除我之外的几位则已经都适应了。所以,当我们到了贾家,在贾家酒厂门外那个齐腰深的冬水田边下车时,本人已经晕车了,刚下车,一个趔趄,就头朝下栽进冬水田里了。真是乐极生悲尴尬极了!本来是很高兴要回家的啊!
顿时,我非常意外,吓了一跳,呛了一些脏水,意识到自己没有站稳倒在水田里了,马上用力往上面翻身、站起。旁边的几位看到我出事了,知道我晕车了,就立即出手把我拉上来。幸好,同行的一位家在贾家医院的年青老乡陈燕飞,让我到他的家里去,找出了合适的衣服、裤子给我换上,我才又能够往家里赶路了。
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当时的天气不是很冷,虽然被水淹了,成了落汤鸡,受了一惊,但是没有使我感冒生病。
读者诸君,本人近些年已是花甲之人,年年体检没有病,水陆空的交通工具都能够适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近些年的交通条件很好了,本人不会晕车了。而当年,本人才20岁,正是年轻,精力充沛的时期,反而晕车,又说明什么呢?说明当年的交通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年轻人都经不起那样长距离的摇晃颠簸。
六、跋语
“东灌”,是岷江引水工程东风渠灌区的简称,已经约定俗成,众所皆知。我们简阳是扩大了的灌区,也都通称“东灌”。
本人经历的主要工作就如上述。
此外,还有几项有关的工程,如张家岩水库工程、南干渠工程、北干渠工程、新南干渠扩渠工程、三岔水库工程,本人都没有直接参与,也就没有叙及。
本人在引水工程只工作了两年,即从1970年3月起,到1972年2月份,被当初的大队领导召回,在村小学校教书,因此离开隧洞组为止。
在草拟此稿过程中,本人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内容;查阅了自己保存至今的当年的日记和工作笔记内容;参考了当初的老领导,现仍健在的彭良浩彭老于两年前,即2014年11月编写的《重上龙泉山》一书中的一些数据和情况;还征询了冷兄。
在此,本人要真诚地谢谢彭老和冷兄二位,谢谢当年的领导和同事们,谢谢曾经支持、关心、帮助过我的所有的人们。顺颂大家吉祥安康!
本人草拟此文,时隔已久,若有不当,敬请指正。
几十年来,每当想到自己当年为造福千秋的引水工程而工作过,每当看到清澈的岷江水在干渠里流淌、在田野里浸润、在龙泉山南麓的几座湖里荡漾,自豪的心情就会油然而生。
由于本人一直以来都喜欢文学,所以退休以后的近几年,经冷兄引路进入《中华诗词论坛》的大门,去向诗词行家们学习有关格律诗词的知识,才对格律诗词有了一知半解。于此,本人草拟拙作一首,作为本文的结语。
七 绝
龙泉吟
二0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隧洞轰隆碧水流,
岷江造福万民讴。
而今复笔书前事,
奉献青春壮志酬。
附录:
《水调歌头 · 重上牛心山》
离开东灌工程以后的几十年里,本人曾经多次想到,重游当年工作过的地方,看看情况怎样,以慰怀旧初衷。二0一0年十二月十八日,终于有了机会,本人在时隔38年后,到了工作过的几个地方游览。故地重游,以致兴起,提笔小吟,凑成一词,难忘当年,念之纪之。
水调歌头
重上牛心山
二0一0年十二月十八日
早思酬意愿,
再上此高山。
光阴如箭,
情景弹指已新然。
草木葱茏繁盛,
凤鸟自由飞隐,
异兽荡林间。
蜿蜒水泥路,
似画白云端。
逢年旱,
耕农盼,
寝难安。
简州眺望,
除旱几日灌梯田?
二万英雄凿洞,
千里岷江送水,
民众尽开颜。
浩浩川中境,
五谷笑声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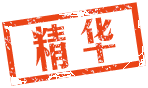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