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婆老家住在川中地区一个依山临江、风景秀丽的小镇上。那个地方有一些奇特的四川方言发音,比如外公、外婆叫家公、家婆,而家字读音不读家(jia ),而是读做嘎(ga ),叫嘎(ga)婆,吃饭叫期(qi )饭,吃肉叫期(qi )嘎嘎。没有研究过四川方言,不知有何历史渊源和出处。 从儿时有记忆起,家婆就是一个疯子——用现在的文明用语是叫精神病患者。但那个时代就叫疯子,精神病院也叫疯人院。 家婆一大早就要出家门,挪动她那双裹缠的小脚,柱着一条木头拐棍,在小镇上的青石板路上步履蹒跚的从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累了饿了,就回家喝点水吃点饭,然后再出家门。无论春夏秋冬,天晴下雨,早出晚归,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开始母亲还跟着,后来时间长了,家里我兄妹四人还小需要照料,也只得由她去了。说也奇怪,我记忆中家婆从来没有感冒生病过,后来听人说疯子身体有特殊的抵抗力,这话有道理。 晚上回到家中,家婆总是很晚才睡觉,一双浑浊无神的眼睛呆望着天花板,嘴里一直不停喃喃的念叨,我凑近了仔细听,听清了家婆一直反复念叨的就是一句话“狗日的耿麻子,告你!狗日的耿麻子,告你!”。 我问母亲,耿麻子是谁,家婆为什么要告他。母亲说,耿麻子是当时镇上来的土改工作队长,北方人,长了一脸的大麻子,镇上的人都叫他耿麻子。家公家婆以前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铺,耿麻子来了以后,就把家公家婆的杂货铺没收了,然后家公就病死了,然后家婆就气疯了。从此以后家婆天天在镇上转,就是想找耿麻子。耿麻子搞完土改早就不知调那里去了,那里找得到他人。 有一次母亲带我到镇上供销社打酱油,出门时悄悄对我说,供销社的这两间铺面以前就是你家公家婆的。后来家里但凡有去供销社打酱油买醋的事情,我都争着跑腿,打完酱油还舍不得马上走,还要东张西望再看两眼,害得供销社的售货大娘总是用警惕的眼光打量我,怀疑我要偷她东西。 家婆没有读过书,除自己的名字外大字不识一个。但却特别喜欢写“字”,家里可以写字的纸都被她写满了奇怪的“字”,边写还边念叨“耿麻子告你!耿麻子告你!”。我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书包要藏好,不然作业本就要被家婆扯去写“字”了。可是家婆写的“字”谁也不认识,我专门研究过她写的“字”,一个个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全部是由横和竖组成,还很少有重复的,我横看竖看,没有一个字是我认识的。有一天我偷偷拿了一张带到学校给小学语文老师看,老师戴上眼镜审视良久说,这肯定不是汉字,应该是一个与汉族有渊源的少数民族创建的只有他本民族才看得懂的字。你从那里弄来的?我没有告诉老师,回到教室一个人偷偷笑了好久。 有一天,家婆突然离家出走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就带走了她写的一大摞“字”。全家人都急坏了,发动邻居、亲戚八方寻找,都没找到,也没有一点消息。小镇边就是一条大江,全家人都认为家婆凶多吉少。 十多天后,家婆却突然一个人回家了。母亲说家婆回家时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几乎是爬着回家的。家婆当时衣衫破烂、蓬头垢面,还不如一个叫花子,母亲都差一点没有认出她来。给家婆吃饱饭,洗澡换衣后问她这十多天究竟跑那里去了,她也不说。从此母亲再也不敢让家婆迈出家门一步。 家婆回家后尽管还是天天骂耿麻子,但是很少再写她的“字”了,我也终于不需要藏书包了。 家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去世的。临终前家婆对母亲说,我好想期(qi)一碗和了白糖和猪油的白米稀饭。那个年代白糖、猪油可都是凭票也难买的奢侈品。等母亲东借西讨的把这碗又甜又油的白米稀饭熬好端到家婆床头,家婆已经紧闭双眼,享用不到这碗美味佳肴了。 90年代中期,家婆去世后二十多年后,镇上供销社解散了,清理资产时在档案里发现了家公的铺面房契和几张下面写有家婆名字谁也看不懂的“字”。资产清理工作组落实政策决定把那两间铺面归还给了家公、家婆的直系亲属。没有想到却引起一场遗产争夺官司,那已是后话不提。 折耳兔 2016年元月2日于都江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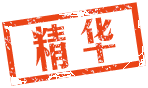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1-2 22:57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1-2 22:57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1-3 10:38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1-3 10:38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1-3 19:46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1-3 19:46